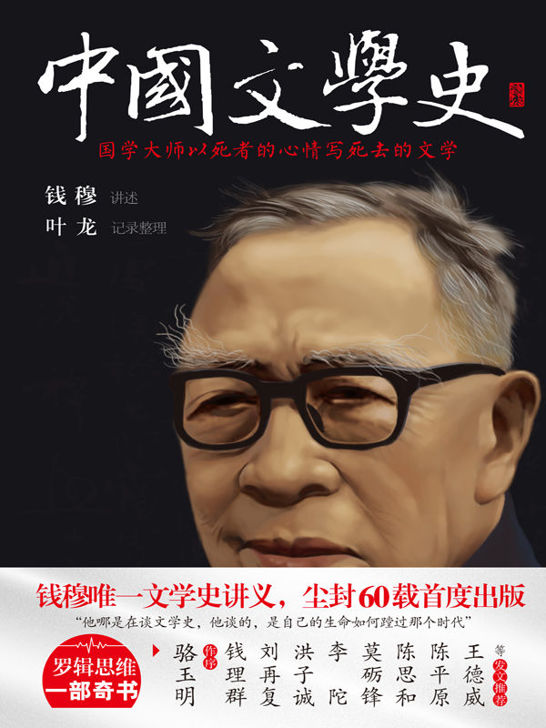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九篇 楚辞(下)
讲起文学,可以分别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时代性的,是纵的;另一方面是地域性的,是横的。
文学是人类从心灵中发出来的表现。它是受着地域的限制的,地域方面最重要者包括气候和山川、风俗等。真实的文学来自广大的群众,须采自当时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学的创造尚需加上技巧。《楚辞》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学性的,是南方文学。
文学的地域性来自民间,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其中“颂”的部分占很少;“雅”代表着来自陕西的声音,其声乌乌然,自有其地域性;“国风”有十五,其声更多了。关于这方面,可参看《汉书·地理志》,这书根据不同地域而说明其风土人情。
孔子最喜爱“国风”之“二南”。当时的诗可唱,所以文学与音乐有关,孔子尤爱南方的韶乐,有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齐国之有韶乐,乃来自陈国。陈在河南淮水流域一带,为舜之后裔,“二南”即南阳今河南与襄阳今湖北之汉水流域。根据古代地理状况,陈与“二南”是属于同一条交通线上的。当年楚怀王败于秦被掳,楚人逃到安徽寿县一带,此时之楚人经过大迁徙,已变为安徽、江苏人矣。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尚有东楚与南楚,逃到湘江流域的是南楚,但人数很少。今日吾人在长沙、寿县一带,均可发现楚墓。故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文字是死的,地域是活的,两者必须配合起来讲。所以,如欲懂十五国风,必须先懂得其地域环境状况。例如,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南方如屈原投水而死,故祭水神时必须用祭物投入水中;北方祭山神则用火烧,使烟上升。孔子之伟大,在于他亦能欣赏南方。陈风与“二南”是轻灵的,北方的则笃实。
《楚辞》随着十五国风中的“二南”、陈风而产生,故其发源之背景是汉水流域与淮水流域,其风土人情自与北方有所不同。
汉代以后的人说,屈原流放到湘江流域,因而以为《九歌》是在湘江流域的背景之下而创造的。此说实违背事实真相,《九歌》的素材并非取材自湘江之洞庭湖。其实屈原《楚辞》之文学创作背景是源自“二南”即襄阳与南阳,即是在湖北而非湖南,因屈原时代所说的洞庭湖与湘江都在鄂湖北,只是因地名的迁徙而造成了误会(注:编者按:《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唐成玄英注:“洞庭之野,天地之间。”历史上有时把地跨长江中游南北的云梦泽跟洞庭湖混而为一。)。
我国任何水名、山名或地名,其命名均有其原因,并非偶然。例如北方的水声浊,故名称有“洛”“河”等音,如名叫洛水、黄河等;南方则水声清,故称“江”,如长江等。然则何以称为“洞庭”呢?因为院子前面的叫作“庭”,是空的;洞者,通也,如称“山洞”“洞箫”等。因此,水相通者叫“洞庭”,所以,凡此水通彼水的均叫“洞庭”。据说太湖也叫洞庭湖,“洞庭”是个通称,是普通名词。我们如去查地理,便可知长江以北亦有洞庭,这正如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两地的山名相同。《尔雅》解释道:“大山宫小山,霍。”意即小山为大山所围叫作“霍”,其理相同。
何谓“湘”?湘者,即相也。正如“襄”,即“相”也,读音相同,两字都是“帮助”之意。王莽时改“相阳”为“襄阳”。《尚书》云:“浩浩怀山襄陵。”此处“襄”字有“凌驾于上”之意,意即水上了陆地,上了山。汉水即是如此,张之洞及以前的大官都曾筑堤来防汉水即襄水。“汉”者,天水之意,天河名叫汉,故汉水即天水,亦即是襄水。
《楚辞·渔父》篇云:“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太史公司马迁认为此句有语病,人在鄂而何以会在湘水自杀,故改为“宁赴常流”。这里又牵涉到校勘学。参看《渔父》篇,襄水又叫作沧浪之水(注:钱按:见《楚辞·渔父》。),可见此文系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此处所说之“湘流”实指“汉水”也。
又如《九歌》云: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此句如形容岳阳楼之洞庭即不配衬,因境界不同;屈原是祭二水神(注:钱按:二水神即二女神,亦即舜之二妃,即汉水之神,《诗经》亦说及。)。屈原作此诗之背景是在湖北。
“橘逾淮为枳”,我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橘是“江陵千树橘”。地名亦可搬家,如英国的地名今日在美国亦有,我国亦然。“洞庭”亦可搬家,并且水与水可相通,故湖北亦有洞庭湖。
中国的字和命名都是有意义的。如“华山”之“华”,意即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思是“二山相并”;“衡山”是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以上所说是文学史上的考据问题。总而言之,屈原所说之湘江与“洞庭”都不是在湖南的,实在是指汉水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