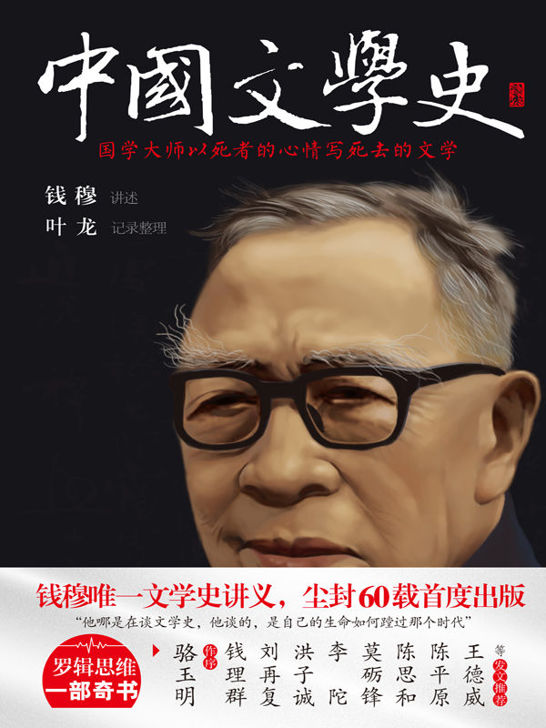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十四篇 汉代奏议、诏令
奏议是政治上应用的散文,人民有意见时写文章上书给政府。
诏令是政府写给民间,只简单讲说几句。
奏议是人民对某件事可详尽申述对或不对,是人民反映给政府的意见。皇帝在诏令中虽可用命令式的语句,但书写的语句中亦可加入情感,使人民悦服,不必用道理、以教训口气来压服人民。
贾谊能写出最高级的政治文章,他的《陈政事疏》《过秦论》及《论积贮疏》等文,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明代归有光赞扬贾谊的《陈政事疏》,何止是西汉第一,简直是“千古书疏之冠”。姚鼐也赞贾谊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连鲁迅也说他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黄东发(注:编者按: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1213-1280)。宗朱子学,曾任史馆检阅。)评说道:“贾谊天资甚高,议论甚高。惜不闻孔子之学。”但贾生在其文中常提及应“与民休息”,应“亲民如子”,主张鼓励农民生产,倡导轻田租等等。他在《陈政事疏》中建议要降服嚣张的匈奴,还主张削弱诸藩,无不是为国爱民的好政策。他的《论积贮疏》对后世影响更大。他慷慨陈述道: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贾生的这种笔势纵横的政治文章,言简意赅,笔力雄伟而凝练,处处表露出其关怀国家、体恤人民之爱心,如果不是周勃、灌婴这班大臣因妒忌而在文帝面前进谗陷害,再加上长沙王的早逝,致使他于青壮之年抑郁而亡,本来他将有一番大作为的。
晁错也是一位善于写奏议文章的人,如他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论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都是他的著名篇章。方苞称赞他的文章与《管子》类近,说他杂用管子之语,如出一人之说。
晁错的《论贵粟疏》向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同时又主张“入粟受爵”。此文中云:
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因此,文景两朝都采用晁错建议,国家遂日益富庶,到武帝时,以至造成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现象。
又如晁错的《守边备塞疏》及《论募民徙塞下疏》等文,并不主张“派远方之卒守塞而一岁一更”,乃是选常居者前往定居,而有家室田作,让守边塞者可安心长期居留屯戍。此所以后世常用屯田屯兵之法以守边疆,可能受晁错之影响不小。可惜晁错在景帝御史大夫任内,建议削诸侯封地,造成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不得已用爰盎(注:编者按:《史记》写作袁盎,《汉书》写作爰盎。)言将其处决。不然会有更多作品留传后世也。
此外,像董仲舒,亦为写奏议文章的高手。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作《举贤良对策》三篇,讨论天人相与、阴阳灾异诸问题,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仲舒文》。
至诏令文,贾谊亦是写此种文章之能臣。等到曹操出,能把诏令写得长,且是用故事体的写法,这使老百姓在阅读时大为增加兴趣。
如,曹操于建安年间赤壁之战时,重挫于孙权、刘备的联军,于是下《求贤令》道: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本来一国的领导,于危急之秋求才若渴,其诏令一类的文章,必定出于庄重严肃的口气,曹氏笔调却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如文中提及一位道德败坏分子,魏无知介绍那位曾与嫂子私通又接受过贿赂的陈平给汉高祖刘邦,使刘邦颇为迟疑,魏无知对高祖说,现在正是需才孔急之时,与德行有差错无关,我推荐的是他的才能,刘邦才重用陈平。
在堂堂正正的诏令文中,任谁也不会把这样的负面故事写进去,但曹操却毫无顾忌,无所不谈。这就是他的浪漫豪爽个性使然。
而且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真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之所以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因为他平日读书多。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就提到了孔子《论语》中赞“齐文、晋文之尊周”,周公《金縢》之书,乐毅闻图燕而垂泪,介之推归隐绵山,申包胥哭秦庭而事成不肯受赏,以及蒙恬之尽忠守义等典故。故吾人读曹文而感兴趣盎然,全由于曹操之勤读典籍、烂熟史事所致,绝非胸无点墨写来空洞乏味可比也。
至曹操写奏议文,如为增封荀彧,作《请增封荀彧表》,全文据实直言,绝无浮华虚语,故《文心雕龙》亦赞其“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乃值得一读之作。
诏令之外,尚有一种名叫“书札”的文体,也是应用文的一种,但汉代时人写“书札”的不多。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注:编者按:此文收入《文选》第四十一卷。)写得极好,亦值得一读。今择要摘录《报任少卿书》部分如下,以供欣赏: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未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
仆与李陵……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所以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关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体大精思而成为我国最伟大的散文杰作,前已有述。此信乃其友任少卿劝其推贤进士,致使太史公满腹怨愤,畅所发泄,坦言是为了广主上的言路,且李陵确实不失为一位国士,可能在万不得已下临时投降敌方,但从他为人看,将来绝对有可能得其当而报汉。可惜事与愿违,世态炎凉,既已惨受腐刑,夫复何言,而主上事后又重用他任中书令,更使他含垢受辱,悲愤欲死,不得已遂继承父志完成《史记》,以泄其郁怒之气。太史公在此整封书札中,只是与挚友畅谈其个人遭遇与抒述其愤懑不平之胸怀。我小时候,十岁左右吧,老师教这封信札时,都是要我们背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