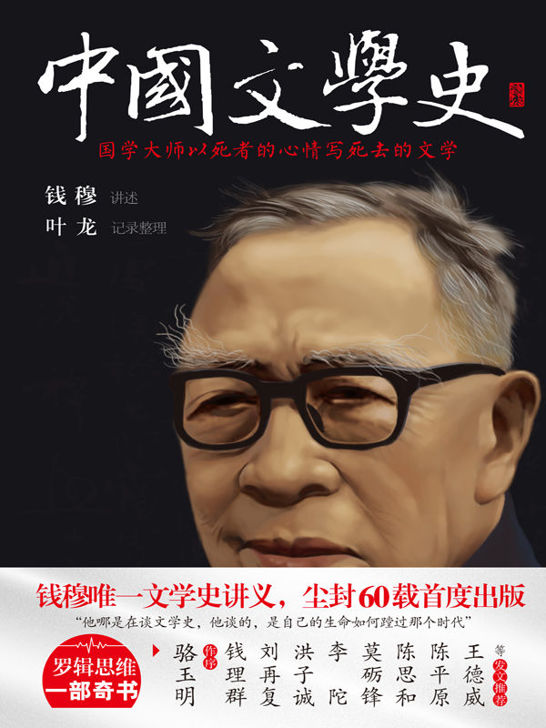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谈到文章的体类,应从三方面讲起。
(一)文学的内容。
(二)文学的对象。
(三)文学的工具与技巧。
谈及文体便不出以上这三条路。
文学的内容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此是指的言,是作者要讲的话。
文学的对象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对方,这是指人,就是作者要讲给谁听。
文学的工具与技巧是作者所要求表达的运使,这是指文,就是作者要如何去讲。
《论语》说:“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论语》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即我们对“中人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谈高深的理论,对“中人以下”的人,则不可以同他谈高深的理论。
《论语》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说,讲话要直白,这是通常的情况,但有时候讲话则应“曲”些“文”些为妙,如直讲则听来就没有意味了。可以一层意思分两层来讲。我国古代的文学由《诗经》到史,到诸子,到《离骚》,到《楚辞》,再到五言诗……这是文体在变,这是文学史上的大问题。
谈到文学的内容,它可以包括说理、记事与抒情各类。“说理”指孔、孟、老、庄、墨等诸子;“记事”指《史记》《汉书》等史著;“抒情”指《诗经》《楚辞》及五言诗等作品。
就文学作品的说理言,第一,要真实。说理的要表达真理,写历史要撰写信史,抒情的要真情流露。
第二,要自然。其实文学作品除了说理、记事和抒情以外,尚须加上“言志”。因为《诗经》三百首是言志的,与抒情有所不同。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照字面看,这是抒情,但这是元帅所作,而非小兵所作,其意是元帅体恤士卒,使士卒高兴。所以是含有政治作用的。
又如《诗经·周南》的《关雎》诗中所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是讲有一位青年男生爱上一位身材苗条、容貌美丽的姑娘,这男孩时刻想念着她,即使在梦中也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还是想着她,希望成为一对好配偶。这表面上是抒情,实际上也是在言志,是讲文王之德化,亦是讽刺康王之晏朝。其实《诗经》三百首,都是有政治作用的上层文学。
《诗经》的国风,这风是指十五国的风,都是当地的乡土民风。由采诗之官去采,可能《关雎》一诗在周南被采去后,经过整理发表,用作另一番道理。因周康王不早起,其后命其早起办事,说如不早起便是我为后之罪,便非淑女也,劝说他不要为了迷恋爱情而耽误了政事。这就是讽喻,也即是言志。
可以说,中国有真正的文学当自建安时期开始。至宋元时代才有西洋文学之体裁风格。在先秦诸子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各家,各家思想不同,故其文章亦不同。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是教育家,都是最会讲话的人。
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回答人的方法亦是如此,孟子、荀子亦都如此。即所谓“夫子时然后言”,“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亦相当有道理。
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有的人不配与他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但孔子的态度是“知我者其天乎!”。
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庄子形容墨子之言是“强聒而不舍”,就是硬要对你说。
孔、孟、老、庄的意境高,至于纵横家、小说家和法家等,就低了。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说理的文章要面对广大的人群,如墨子之喜为大众讲话。孟子则不然,他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至于西方的,如荷马和苏格拉底,他们是面对群众的、社会的。与中国的《诗经》之针对政治圈子,诸子的针对学术圈,均非为社会大众不同,所以中西文学是有所不同的。
再讲到记事方面,是指历史著作,可分官史和私史。《春秋》是一本官史,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太史公的《史记》,是私史。他修史的宗旨是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它并不是放在国史馆中,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待将来给后人看的。
中国人重视写史的自由。立言是三不朽之一,写史就可立言,为的是要在历史上留名,却并不重视天堂、灵魂这一套说法。
曹丕曾出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所以周文王演《易》,周公作《周礼》,其名流芳百世。
曹丕认为建安众文友,他们的体貌与万物同归尘土,乃人生之大痛,惟有徐幹著有《中论》一书,足以留名后世,成一家之言也。
至于抒情的文学,《离骚》可以说是中国有纯粹文学的开始。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虽然谋国以忠,事君以诚,却被上官大夫那班小人所谗害,致被怀王所疏远。屈原遂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抒发他的愤懑不平之气,以冀怀王感悟。惜襄王时复用谗,屈原被谪放江南,终自沉汨罗江而亡。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屈原的《离骚》色而不淫,诽而不乱,可谓兼而有之。他怨得纯真而自然,而超越了他的现实人生,但不会出乱子,所以是好文章。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情况时,就当看作是行云流水一般。
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如太史公的《史记》和《孟子》以及《庄子》等作品,其作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
文学又是时代的,如《孔雀东南飞》这首一千七百多字的长诗,描写东汉时焦仲卿夫妇同殉的事迹。焦妻刘氏自誓不嫁,为焦母所逼,投水而死,焦仲卿亦随之自缢而亡。这只是小生命,但与时代无关。大生命是有时代性的,它不但有内在的生命力,而且有外在的生命力。
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老子所谓“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孔子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总之,文学的境界是面对有人,但面对无人是最自然的境界。《离骚》是有怨,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如屈原的弟子、楚国大夫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其赋曰: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于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以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寐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人谓宋玉为屈原弟子,或称为后学,但此作亦具有爱国思想,确是模仿前人之作,亦有其生命,但并无大生命与时代感,故文学之创造不易,模仿亦不是易事,但仍是要模仿,只是与创造不同。
到汉代,则有司马相如、扬雄辈出。
司马相如的文章,其修辞、造句、谋篇及布局均臻上乘,且有时代性,代表了汉武帝的大一统,如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均写得极佳,描写出整个时代性,也略有自然与生命的气味。
今摘录《子虚赋》一节如下: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畋,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其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獲猱,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畋,乃欲勠力致获,以娱左右,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崒,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
可知司马相如作赋,极尽其铺张夸大的能事,例如上文《子虚赋》中描写云梦山,自“云梦者,方九百里”开始,直至“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其中引用了各种珍禽怪兽、奇花异草,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如何、水如何,其铺辞丽靡,实过于藻饰,但迎合于此一时代的风格。
今再摘录司马相如《上林赋》数节于下: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
……
“于是乎周览泛观,缜纷轧芴,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橐驼,蛩蛩,驴骡。
……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罕,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
“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
以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都是名篇,其辞藻、结构均属优秀之作。
再说扬雄,也是汉赋鼎盛时期的名家。他们当时描写的都是汉武帝以来的强大国势,物产的丰饶,宫苑的富丽堂皇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盛况。扬雄的《羽猎赋》说:
孝成帝时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胡……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其辞曰:
或称羲、农,岂或帝王之弥文哉?论者云否,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则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仪?是以创业垂统者俱不见其爽,遐迩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訾,贵正与天乎比崇。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严未足以为骖乘……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
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帝将惟田于灵之囿,开北垠,受不周之制,以奉终始颛顼、玄冥之统。
……
于兹乎鸿生巨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响忽如神。仁声惠于北狄,武谊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享,抗手称臣。前入围口,后陈卢山。群公常伯阳朱、墨翟之徒,喟然并称曰:“崇哉乎德,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觐东岳,禅梁基,舍此世也,其谁与哉?”……
扬雄又有《长杨赋》,也是写的畋猎。
司马相如在梁孝王时代曾加入梁园文学团队,作《子虚赋》,梁孝王逝世,梁园文社随之解散,司马相如亦返回乡居。至汉武帝即位,偶读其《子虚赋》,喜好之,遂召相如回朝。他对武帝说,《子虚赋》只是叙诸侯之事,并无精意可言,今请为主上作畋猎之赋,遂作《上林赋》,武帝大喜,并封相如为郎。《子虚赋》与《上林赋》两赋之完成,相距十载。但两赋内容贯通相连,世人谓二文实二而一。《子虚赋》写楚臣出使于齐,齐王盛情款待,一同出猎。此文描写齐王畋猎之盛,并同时讲述楚王游猎云梦盛况,文中借乌有先生之口批评子虚不重君王以德义治天下,而大谈游猎盛况,斥为不当。至于《上林赋》,乃承接《子虚赋》,以亡是公口气批评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漠视民生而奢侈游猎之不妥。两文波澜壮阔、气势宏伟,为汉赋典范之作。
至于扬雄的《羽猎赋》和《长杨赋》,亦是西汉末年时期之名作。他早年喜好辞赋,崇奉司马相如,晚年则视辞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也。至于《羽猎赋》和《长杨赋》两赋,则深受司马相如之影响,是为成帝爱好游猎而作。但不论如何,这些作品都突显出当时的时代性。
郭沫若说,他根据商代的甲骨文,断定商代为游牧时代,但他只是取些片面的材料。畋猎只是当时贵族生活中的最高奢侈与最高娱乐。
可以说,汉赋是传承宋玉而来,而并非传承自屈原,自此而走上纯文学的道路,因诸子的孔、孟、老、庄之书和《史记》等均非纯文学,汉赋则是歌唱时代的文学。到东汉时,人生观与文学思潮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则魏晋后的新文学,又是一番新的风貌了。
如上所说,文章的体类有言志、说理、记事和抒情四种。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随时代而产生悲观心理,他们不想要留名,亦不是走向政治或学术园地,所谈不外乎男女的悲欢离合与生老死别,自然地流露其悲观的情绪,故代表了一个时代,对其生命从根本处看,是消极的,对人生一无价值。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赋》。(注:编者按:《寡妇赋》小序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
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