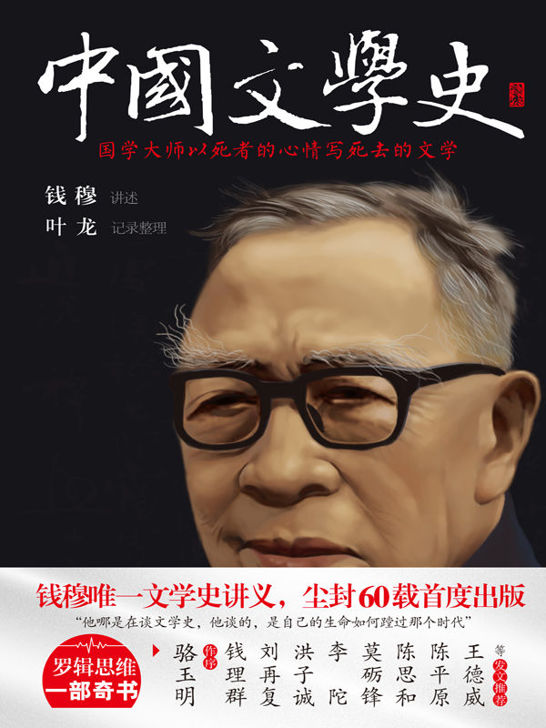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十九篇 昭明文选
《文选》为梁萧统所编纂。萧统为梁武帝萧衍长子,于和帝中兴元年即西元501年生于襄阳,次年萧衍即位称梁武帝,同年立统为皇太子。统资质聪慧、文思敏捷,九岁能讲《孝经》,事母至孝,他年轻时,其父皇命其处理政事,仁名远播。惜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谥为“昭明”,故名是书为《昭明文选》。
在齐、梁时期,编纂诗文总集的风气很盛。编选的学者文人多不胜数,如晋杜预有《善文》,稍后李充有《翰林论》,西晋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宋刘义庆有《集林》以及沈约有《集钞》等等。这些选集由于时代较久远,所选文类及篇数不及《昭明文选》之丰富齐全,且昭明太子在财力物力人力各方面占了极大的优势。
昭明太子出身于皇族,自幼酷爱文学,藏书数万卷,又礼遇天下学者文士,并且,在东宫担任官职的,如任职通事舍人的刘勰,都是他所器重的,可谓人才济济,群贤毕集。有如此多的学者文士担任他的顾问或直接参与实际的编选,在先前的众多选集或因文体分类不足,或因选文欠丰亦欠精准,逐渐先后淘汰之后,《昭明文选》于是成为当时诗文总集的独存孤本。前面已讲及,如欲研究古代诗文,则取《诗经》与《昭明文选》两种已经足够了。
关于《昭明文选》的体例,在其《文选序》中已有详细说明,全序可分八大段,今试分段析述如下。《文选序》首段道: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以上《文选序》之首段是说,在上古原始时期,人们住在洞穴中或在树上筑巢而居,他们茹毛饮血,文化尚未昌明,要到伏羲画八卦,造书契,才有文字以代替结绳记事。《易经》上说:观察天文可知四时季节的变化,观察人文以向百姓施行教化。这说明文章的深远时代意义由此开始。接着,《文选序》的次段说: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注:编者按:椎轮,无辐条的车轮。大辂,天子乘用的车。《礼记·乐记》:“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这段是说:像椎轮这种粗陋的工具,原来是制造大辂的先导,大辂的质地精细,但没有椎轮的质朴。厚厚的冰块是由积水凝结而成,但当初的积水不会如冰块那么冰冷。这是由于天下的事物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它改变了原来的样貌,增加了新添的效益,天下的事事物物都是如此。文章亦如此地随着时代变化,这是难以详细了解的。
《序》的第三段说: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这一段谈到《诗经》有风、雅、颂、赋、比、兴六种体裁,但现在的文体已有变化。赋本来只是《诗》之一义,现在的文章则统称为赋了。先有荀子、宋玉开导于前,再有贾谊与司马相如承袭在后,从此赋的发展十分繁富。如托借凭虚公子和亡是公来描写宫殿;又有《长杨》《羽猎》诸赋劝诫君王游猎的。至于单记一事、咏一物,或对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描写文章则不可胜数了。此外,如屈原这样态行高洁的人,楚王竟不纳谏,遂使他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临终前憔悴行吟泽畔,致有《离骚》之作产生。
《序》的第四段说: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
这一段讲的是:《诗经》本来是述志的,心有所感便发之于文。如《关雎》《麟趾》等诗,志在宣扬圣王教化之道;《桑间》《濮上》之诗,则是亡国之音。当时风、雅的作品大为盛行,但自汉代中叶开始,诗歌的发展已与往昔不同。韦孟在邹作闲居之诗;李陵则写了“携手上河梁”的诗。自此,自四言、五言之诗发展到三言、六言、七言以至多达九言之诗,都分头发展兴旺起来。颂是用来歌功颂德的,尹吉甫作“穆若”以赞美周宣王,吴季札对颂乐大加赞赏,这一切,都是用来颂扬人之美德。
《序》的第五段说:
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此第五段是讲到各种文体之创用原由,“箴”是为了补救缺失,“戒”是为了纠正错误,“论”则是要精细地去分析事物之理,“铭”是叙事要求清通圆畅,“诔”是为寿终者作的美文,“赞”是为图像作赞扬文章。此外,如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以及书札、誓词、檄文、祭文以及答客和指事一类的作品,还有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文行状这些不同体裁、种类繁多的文章,都相继丛生,就像各种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各自发出悦耳之声,亦似各种花纹各异的服饰,使人都能欣赏悦目。文学家亦能借着其所创作的各种不同文体,表达其辞藻意境之美。
《序》的第六段说: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这第六段的意思是:我在担任监国、抚军之余,便可利用这许多闲暇时间遍读群著,即使费时久长亦不知倦。计自周、汉至今,已更换了七个朝代,历时一千余年。多少文人才子名满闹城僻乡,多少诗文名篇充满于卷帙中,当然非把那些芜杂的文稿抛弃不可,只能留下精彩的,不然,哪里有许多工夫去遍读呢!
《序》的第七段说: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此段意思是:像周公、孔子的经典,如日月照耀于天地之间,似鬼神般奥妙,所论都是人生伦常道德的规范,岂可任意删剪裁削?至于老、庄、管、孟之书都以理论为主,不重文采,故亦删去不选。
《序》最后的第八段道: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注:编者按:坟籍,泛指古代典籍。坟,概指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张衡《东京赋》:“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薛综注:“三坟,三皇之书也,五典,五帝之书也。”),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此末段说明:像贤人所言,忠臣直谏,谋士言辞,辩士舌锋,滔滔不绝地义法兼顾,如喷泉一般涌出来。似田巴(注:编者按:田巴,战国时齐国辩士。)在狙丘的论辩、在稷下的议论,又像鲁仲连说辞退秦军,郦食其招降各国,张良反对再复封六国而发《八难》,陈平六出奇计,为时人赞美而流芳后世,子、史典籍争相刊载,由于文辞繁富,不及备载,亦不同于文学,故亦不选入。至于记事体和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有别的也除外,但有些属于赞论、序述,似属优美的辞藻,则一并杂入其中。最后说明选文的体例编排和先后次序。大体上说,全序说明了全书的选录和如何分类编排,但以文采和辞藻为主。
有关《昭明文选》的篇章分类,可能是自古以来分类最细最多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只是分了二十类,但《文选》竟分了三十八体之多,分列述于下:
(一)赋体:下分十五类
1.京都
2.郊祀
3.耕藉
4.畋猎
5.纪行
6.游览
7.宫殿
8.江海
9.物色
10.鸟兽
11.志
12.哀伤
13.论文
14.音乐
15.情
(二)诗体:分二十四类
1.补亡
2.述德
3.劝励
4.献诗
5.公䜩
6.祖饯
7.咏史
8.百一
9.游仙
10.招隐
11.反招隐
12.游览
13.咏怀
14.哀伤
15.赠答
16.行旅
17.军戎
18.郊庙
19.心吊
20.乐府
21.挽歌
22.杂歌
23.杂诗
24.杂拟
(三)骚包括《楚辞》
(四)七
(五)诏
(六)册
(七)令
(八)教
(九)文
(十)表
(十一)上书
(十二)启
(十三)弹事
(十四)牍
(十五)奏记
(十六)书
(十七)檄
(十八)对问
(十九)设论
(二十)辞
(廿一)序
(廿二)颂
(廿三)赞
(廿四)符命
(廿五)史论
(廿六)史述赞
(廿七)论
(廿八)连珠
(廿九)箴
(卅)铭
(卅一)诔
(卅二)哀
(卅三)碑文
(卅四)墓志
(卅五)行状
(卅六)吊文
(卅七)祭文
(卅八)笺
以上《文选》之三十八文体中,有若干条须在此稍作解释者,析述于下:
(一)赋体
◆赋体1“京都”,即指帝都。如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二京赋》即《东京赋》《西京赋》及左思之《三都赋》等。
◆赋体2“郊祀”,指君王祭天。
◆赋体3“耕藉”,指君王之礼节,如亲自下田。
◆赋体4“畋猎”,指君王之娱乐。
上述之2、3、4三类有司马相如所撰《子虚赋》《上林赋》,扬雄所撰《羽猎赋》及《长杨赋》等。
◆赋体6“游览”,有王粲《登楼赋》等,有了新体裁后,已不讲帝王,而讲私人。
◆赋体7“宫殿”,指描写外观的。西汉时鲁灵光殿,到魏晋时仍存在。东汉时王逸有子(王延寿),逸当时想为此殿作赋,逸子亲自去曲阜,考察该殿,以便父做写赋资料。后来逸子自己写了一篇,他已写,别人便不再写了。(注:编者按:据《后汉书·王逸传》记载,东汉蔡邕也想以鲁灵光殿为题材写赋,但见到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也就不再写了。)
◆赋体9“物色”,指描写风、月、雪、秋等。
◆赋体10“鸟兽”,有描写鹦鹉、白马的。
◆赋体11“志”,如张衡之《归田赋》、潘安之《闲居赋》及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等。此类文与“哀伤”无甚分别,乃来自生活中之感受。如张衡之《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是指作者游京都不遇,身怀良才不为君王所用,有不如归家之感。因不遇而不得志,遂兴起归家之念,此种并非谈修齐治平之道,而是写日常生活之遭遇。如陶渊明之《归去来兮辞》,即是“归田赋”,为过去先秦文学所无,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一套文化价值,且是根深蒂固的。
◆赋体12“哀伤”,指怀念朋友之逝去,如《思旧赋》《叹逝赋》等赋均属此类。
◆赋体14、15之“音乐”与“情”两类放入赋体中,因文章、音乐仍是属于情志一类也。
综言之,汉代人的是旧赋,建安以后的则是新赋,内容有所不同。
(二)诗体:分二十四类。
◆诗体2“述德”是讲先祖之事。
◆诗体3“劝励”是指勉励对方。
◆诗体5“公”是指请酒时即席赋诗。
◆诗体6“祖饯”是指送行。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即是送行。
◆诗体7“咏诗”指寄托于描写历史上的人,心中有事,以史诗表之。
◆诗体8“百一”,此类诗只有一个人曾作过,是对政治问题而发,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指对政治上或有百分之一的贡献。
◆诗体9“游仙”指老、庄思想,描写仙人思想。
◆诗体10“招隐”指招隐者出任。
◆诗体13“咏怀”,阮籍首先写此类诗,写心中所怀之事。
◆诗体16“行旅”指游览时在路途中。如“清明时节雨纷纷”之类的诗。
◆诗体20“乐府”指民间所唱的诗歌。
(三)“骚体”,亦包括《楚辞》在内。
(七)至(八)、(九)即“令”“教”“文”三体,是指上级对下级。
(十)至(十五)有“表”“上书”“启”“弹事”“牍”含“笺”“奏记”等六体,并非对上级之作。
(十六)“书体”,此类特佳。
(十七)“檄体”,讨伐用。
以上《昭明文选》文章分类的三十八体中,录用作品的作家,自先秦至南朝梁共有一百二十七人,诗文歌赋共采录七百余篇。先秦采用的作家只有子夏、屈原、宋玉及荆轲四位。采用屈原的较多,达七首,宋玉有七首,其余各一首而已。
秦代的仅采用李斯一文而已。
两汉的采用较多。西汉的采录了高祖刘邦、武帝刘彻、贾谊、枚乘、韦孟、淮南小山、司马相如、邹阳、司马迁、李陵、东方朔、苏武、杨恽、孔安国、扬雄、刘歆、班婕妤等十八人的作品,其中采用司马相如的有七篇之多,其次是扬雄的六篇。
后汉被收录文章的作家有班固、班彪、张衡、马融、朱浮、傅毅、史岑、王延寿、崔瑗、蔡邕、孔融、刘桢、阮瑀、潘勖、祢衡、应玚、陈琳、杨修、班昭、繁钦及王粲共二十一人。选入作品最多的则有王粲十四首;班固十一首;刘桢十首;张衡则有五赋四诗,也不算少。
蜀汉则只有诸葛亮《出师表》一篇。
魏则有曹操、丕、植三父子,吴质、嵇康、阮籍、钟会、何晏、曹囧、李康、应璩、缪袭等十二位,其中以曹植的作品占了三十九首,为最多,曹丕的也有九首,曹操则只有《短歌行》《苦寒行》两首而已。
吴只有韦昭一篇。
晋有杜预、羊祜、赵至、傅玄、应贞、枣据、成公绥、向秀、刘伶、潘岳、张华、石崇、何劭、陆机、张载、孙楚、傅咸、夏侯湛、左思、潘尼、陆云、司马彪、张协、李密、曹据、张悛、桓温、孙绰、殷仲文、谢混、陶潜、王康琚、刘琨、郭璞、庾亮、木华、郭泰机、欧阳建、王讚、卢谌、袁宏、干宝、束皙、皇甫谧及张翰等四十五人,其中收录陆机之诗赋达一百一十首之多,被收录作品之多为全书之冠。此外如潘岳有二十二首,左思有十五首。
南朝宋代被选入诗文的则有谢灵运、谢惠连、傅亮、谢瞻、范晔、鲍照、谢庄、袁淑、颜延之、王微、王僧达及刘铄共十二位。其中谢灵运占三十九首,颜延之二十六首,鲍照二十首。
齐有谢脁、王融、王俭、孔稚珪、陆厥、任昉、丘迟、沈约、江淹、范云、王巾、徐悱、刘峻及虞义等十位,其中谢脁被选录二十三首,任昉二十一首,沈约十七首。
大体来讲,越古老的,如周、秦、两汉被选入的个人作品较少,到了魏晋则人数增多,个别作家的作品选入篇数也较多了,到宋、齐、梁三代,作家人数虽不算比先前的多,但个别作家有大量作品被选入的人数则比周秦汉魏为多了。也有人批评这是薄古而厚今,这也是见仁见智的看法,难免见解有所不同。
我国的文学,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可说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其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的产生而已。
《昭明文选》之失败是,其中之“史论”“论”“史述赞”“诏”及“令”诸体不应该用韵文,但“檄”与“哀”用韵文倒是很适当的。《文选》用了很多绚丽的辞藻是值得吾人学习的;又如《文选》中用了很多古旧生冷的字,便使今日没再使用的旧字重新可以活过来,这也值得称道。记得我十八岁时,在家乡教小学,曾选教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文选》中有这些文章,学生常问我难字。让现代人多认识一些已被弃置不用的古老难字,应是一件好事。
南朝宋代用有韵之四六文,甚至政府亦用此种文体。后来欧阳修、苏东坡诸名家亦擅长写此等文章。
清代《曾文正公家训》中谈及,曾文正亦爱读《文选》。
我认为《昭明文选》中所选入的古代诗文辞赋已经相当广泛且多,如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再加上一本《诗经》,业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