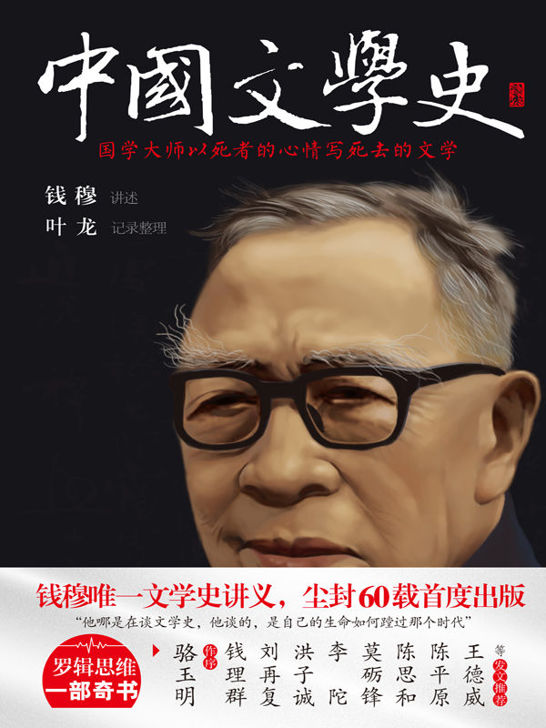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十三编 唐代古文(上)
如欲研究唐代的诗、文,可参考《全唐诗》和《全唐文》;如欲研究唐代小说,则要参考《太平广记》。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古代并无集部(注:编者按:“集部”自唐初《隋书·经志》起确立。钱先生大概指与“经”“史”“子”相比,“集”这种分类法出现较晚。)。明人编有《汉魏百三名家集》(注:编者按:《汉魏百三名家集》,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编。);清人编有《全上古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及《全唐文》。但此后没有“全宋文”、“全明文”。(注:编者按:《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全明文》,钱伯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开始出版;另,《全元文》,李修生编,凤凰出版社出版,2005年。)
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凡经学六经皆史及史学,均可用于政治,而并非明道、辨道、论道。如屈原、司马相如是纯文学家,但他们所作却是韵文而非散文。所以,在韩愈之前,尚没有散文作家。
清代姚鼐姬传在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中,把文章分成十三类。其中的“论辨”类,如贾谊之《过秦论》,是从子部变来。又如“序跋”类,是书之前面的一篇序,本应放在书之最后,称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故放在前面,所以“序”即是“跋”。如《庄子》的《天下》篇放在最后,其实等于一篇跋。“论辨”类和“序跋”类可以归入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又,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奏议”和“诏令”,是政治文集,前者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和《论督责书》,贾生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以及司马长卿的《谏猎疏》,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等,均属“奏议”;后者如秦始皇的《初并天下议帝号令》、汉高祖的《入关告谕》、汉文帝的《除肉刑诏》、司马长卿的《论巴蜀檄》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均属“诏令”文。又如“书说”类,这类文章,战国时有,如赵良《说商君》、苏季子《说齐宣王》、张仪《说楚怀王》等,均是;至汉代则“书说”类不多,只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子幼(注:编者按:杨恽,字子幼。司马迁的外孙。)《报孙会宗书》等少数佳作而已,直到唐宋才有大量佳作出现。姚鼐选入韩愈此类文达二十四篇之多,选入柳宗元的亦有四篇。
尚有“碑志”类,连前所提及的“奏议”“诏令”与“书说”类,则可划入经、史、子、集中的“史部”。世称立石墓上曰“碑”、曰“表”,埋入土中曰“志”,或分成“志”与“铭”。东汉蔡邕伯喈善作此类文字。姚鼐选入韩愈此类文亦特多,几近三十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点是,魏晋后中国人重视韵文,辞赋之文大盛。亦即建安以后,文学的地位提高,人们看重辞赋韵文,故魏晋后之著作,“奏议”“书说”“碑志”这几类文都用韵文写。如《文心雕龙》,书名本身便好辞藻,其内容是骈文;又如唐刘知几的《史通》,亦用骈文写成。前者为文学批评,后者为史学批评,均用骈文来写。又如,唐代陆贽是位政论家,他一生写奏议,人称陆宣公奏议,亦用骈文写。
大致说来,自汉代开始,就出现了藻采华丽、音律悦耳的骈文,一直到魏、晋、宋、齐、梁、陈及隋,于是才有韩愈出,由他来文起八代之衰。当时唐代继承六朝余绪,朝野大部分奏疏都用骈文写成,魏徵想加以矫正,但影响力不大,要到韩愈出,才纠正了这一风气。
唐时韩愈之前的有关文章的概念,可有以下四点:一是以前的文学不独立,是属于政治的,是文以载道的;二是中国的纯文学自屈原开始;三是中国的文学分辞赋与经、史、子两大类;四是建安时期后特重辞赋文学,魏晋南北朝后多用骈文写作。
我对上述文学风气,可有数点意见。
一是建安时期曹丕提出文学不朽观念是对的;
二是一切经、史、子的文学不可硬用韵文,因文体不合,应用文不应用韵文来写;
三是中国文章可分为应用文即含经、史、子之文与韵文两大类。
在南北朝时代,政治并不清明,但为文多用骈丽之作。北朝苏绰(注:编者按:苏绰(498-546),南北朝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制定并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出面反对此种风花雪月之文体,不准用绮靡辞藻,主张复古。
到隋代之李谔,提倡公文不许写韵文,文字要庄严。
到唐代,杜甫以诗来推行复古运动,即诗以载道。
到韩愈出,大力提倡古文复古运动,并以文为诗,创出一
条作诗之新路,又以诗为文,成为韩愈之新文体。首先,韩愈的散文可说是纯文学的;其次,韩愈的散文是摆入了日常生活中。如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时,当时潮州距长安很远,古代的交通又没有快捷如汽车、火车的交通工具。他时年已逾五十,冬季被贬,于风雪中行路十分艰苦,当他到达陕西边外的蓝关时,漫天暴风雪,连马也不肯走了,幸得他的侄孙韩湘子救他脱险。韩愈万分感慨,遂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此诗一面抒写其感慨之意,一面也显露其倔强之志,所描写的也是他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段情节。今日的戏剧中,有人创出《蓝关雪》(注:编者按:《蓝关雪》,署名吴下健儿撰,中华图书馆,1922年。)一剧,还有世所传的《八仙闹东海》(注:编者按:戏曲舞台比较流行的《八仙过海》,八仙各显神通。),也是描写韩湘子的,他是其中一位神仙。
韩愈到了潮州后,一方面关心民困,扶危济贫,一方面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工作,又鼓励当地人民男耕女织,使荒僻冷落的农村变成繁荣昌盛之地。但当地濒临南海边的恶溪,有鳄鱼为患,民间所养牛羊几乎全遭鳄鱼残害,甚至生人也要被吞食,于是韩愈用严厉之训斥及强硬的态度撰成《祭鳄鱼文》。名为“祭”,实为“檄”,其文曰: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之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本来对付鳄鱼,应以武力从事,但处此僻壤穷地,不但当时没有现代化之海军舰艇,连渔猎之大船亦无有半只一艘,韩愈不得已用檄文一招,明知是精神上安慰乡民,但为民除害之心却是真诚无讹,而鳄鱼竟愿远遁恶溪归入大海。它们首先是吃饱了,吃了抛下溪中之猪、羊,其他原因可能与当时之气候、风向亦不无关系。俗语说:心诚则灵,潮州人们亦十分了解韩愈关怀民间疾苦之心情。
韩愈,南阳人今属河南省。他三岁已是孤儿,依靠兄长韩会过活。退之自幼努力勤读典籍,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他不畏强权,得罪朝中官员,并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因上书痛陈关中的旱灾,得罪了主上,被贬为阳山令。但他在被贬期中,把阳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亦十分爱戴,把儿女之名字改为“钦韩”“爱韩”等等。当时他还写了一篇《进学解》,当朝丞相裴度看到后,觉得退之才华非凡,遂又设法将他调回中央任官;至唐宪宗元和十年西元815年,他随裴度征讨吴元济有功而擢升为刑部侍郎。可又因宪宗信佛过痴,退之遂作《谏迎佛骨表》以规劝主上而得罪当朝,遂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一心为国,爱民之心始终不二。退之在潮州时,曾上书感恩宪宗不杀之恩,遂调任为今属江西的袁州刺史。两年后,穆宗因惜才将他调回京城任“国子祭酒”,此官相当于今日之国立大学校长,使他得展所长,亦为当时国子监员生所钦佩欢迎。
终退之一生,他提倡恢复古文运动,推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自认为孔孟传人,为文应贯穿孔孟之道。韩愈、柳宗元等力主“文以载道”,与当时政坛的改革新风相结合,成为推广儒学复兴思潮牢不可破的屏障。
还有一点,韩愈的散文已融入于吾人之日常生活之中。这是退之作品的一大特点。他发明作“赠序”,如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文曰: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悔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退之所创的“赠序”散文,显然是以诗为文,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是纯文学的。文中的情味,非议论,亦非奏议、碑志,是无韵的散文诗,情味自与别不同。如诗般的短句,质朴而富美感,看上去像一首诗,读起来更像一首诗,这是退之独创的诗体散文,是抒情文。又如退之之《祭田横墓文》,不用骈体,而是用散文体。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唯退之能打破局限。
还有,韩愈写的《滕王阁记》比王勃写得好。
韩愈的哀祭亦用散文写,如《祭十二郎文》便是。
韩愈亦喜写游戏小品。如他替泥水匠写传,曰《圬者王承福传》;又写《毛颖传》,实系写一枝毛笔;又写《送穷文》,希望穷鬼不要跟随。
写祭文之开始是关乎宗教,如古代祭文、武、周公,是庄严的,敬鬼神的,要唱,所以通常是用韵文体,但韩愈写祭文却用散文体,照理,散文不易抒情,但他却能从散文中抒写喜怒哀乐,可歌可泣。兹录其《毛颖传》第三段: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下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
退之此文发表后,并不讨好当时,很多人笑他的创作不够严肃,连向来赞赏他文章优美的宰相裴度也不以为然。唯有老友柳宗元赞此为奇文,以为值得欣赏。
韩愈有一篇滑稽文章叫《送穷文》,他准备把家中的穷鬼赶走,先准备了干粮、饮水和交通工具,该文是用对话方式,借文中主人与穷鬼对话。话中当然谈到穷鬼的穷伙伴也要一起离开,结果谈到穷伙伴的数量,搞笑的是,主人说:你穷鬼有几个穷伙伴,我是清清楚楚的,其实是五个。但文中不是直截了当地说,而是转弯抹角、搞笑地说:这穷鬼不是六,也不是四,说是十个就得减去五个,说是七个吧,还是要去掉两个。(注:编者按:原文为“非四非六,在十去五,满七除二”。)这似乎是数字游戏的猜谜。假如真是如此,则数字游戏的猜灯谜,也应当是韩愈首创的了。至于文中所说的穷鬼的五个穷伙伴是:
(一)智穷;
(二)学穷;
(三)文穷;
(四)命穷;
(五)交穷。
窃以为,以上五穷,韩愈真正穷的是“命穷”与“交穷”。
怎么说韩愈是“命穷”呢?首先,韩愈三岁成了孤儿,其青少年时期是靠兄长韩会把他养大的,不幸兄长又早卒,最后与嫂嫂相依为命,命运实在太差了。接着韩愈在德宗贞元八年,即二十二岁那年去考进士,遇上当时的文学家陆贽任主考官,考题是“不迁怒不贰过论”,题目出自《论语》的孔子赞颜回之句,照理这应是韩愈的拿手杰作了,但竟然不幸落榜了。这不是命穷便没有别的好解释了。奇的是,翌年韩愈再考,主考官与考题相同,韩愈作的文也与上年相同,但这一次竟为陆贽击节叹赏,竟录取为第一名。这不是和韩愈开了一个大玩笑吗?过去的一年里韩愈的内心是充满酸、苦、辣的,录取那年内心感受为何,也只有韩愈自己知道了。
韩愈考取功名之后,其遭遇也并不十分顺利,他中了进士,先是担任监察御史,可惜他看不惯种种政治上的弊病,加上朝中大臣也多嫉恨他,因此在他上奏关中旱灾为民请命之时,不幸被贬为阳山令,而且前文已有述及,柳宗元与刘禹锡两位老友也涉嫌参与此事,虽然后来有丞相裴度救了他,但一路来,似乎没有一位可以肝胆相照的知心友,所以也可说是“交穷”了。
还有一件不如意的事。韩愈有二妾,据宋·王谠《唐语林》卷六所记: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后来柳枝爬墙垣遁逃,终为家人追获。有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人谓可能退之专宠绛桃所致。宋代陈与义有诗道:“官柳正须工部出,园花犹为退之留。”亦可谓退之生平一件憾事。
还有,韩愈在裴度之助回朝任职后,因写了篇《谏迎佛骨表》而遭宪宗贬为潮州刺史,他写了一首意态苍茫但意志仍坚强不屈的好诗,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因此使后人创出一出《蓝关雪》的名剧。后来韩愈虽然写了一封向宪宗感恩不杀的上书,改调为较近长安的“袁州(注:钱按:袁州在今江西省,距当时的京城,当然较广东的潮州为近。)刺史”,但到穆宗时才调他回长安任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四年,愈卒,年五十岁,也就是安定的岁月度过了不足四年,年还不过花甲,寿命也不算长。退之其政坛地位并没有柳宗元高,虽然韩柳并称,其诗文亦高过子厚,但声名地位都不及子厚。所以,韩愈的“命穷”“交穷”可以说是他真实的写照。不过韩愈前面谈到的“智穷”“学穷”与“文穷”,那都是韩愈的强项,怎么都算不上穷,足以名留千古,也足以自豪了。所以,韩愈之所以写《送穷文》,恐怕只是开个玩笑、做个游戏而已;但从另一方面说,相信韩愈也一定自认为“命苦”“交穷”,那可能是他的真实写照,为自己抒发怨愤牢骚,也很可能是他作此文的另一个目的吧!
最后,还得把韩愈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原道》讲一下,将其中几节摘录如下: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宜,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陈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观此文,韩愈是隐隐然以传扬孔孟之道自居,依照退之一生,无论他是从政也好,写作诗文也好,确实是奉行着孔孟之道,以此作为他的终身的核心思想与为人目标,他是切实做到了。退之绝不是像别人那样,口中说自己才是孔孟的真传人,行为上却拉帮结派,只是为个人和集团的名利打算,而且对金钱私利特别看重,不惜排斥伤害曾经帮过他们的彬彬君子和好友,他不愧为孔孟的继承者。其实,信奉孔孟,任谁都可以,只要他服膺《论语》《孟子》,也便是孔孟之忠实门徒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注:叶龙按:本人在大学求学时,发觉有多位教授都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作风与本文所讲如出一辙。当时钱师十分赞赏商学院的众教授。)
韩愈除了是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他还有另外两大贡献,提出辟佛及提出尊重师道。他特重师道,并撰写《师说》:凡可传道、授业及解惑的都应被尊为师。
再回头来说:五四运动之大毛病,在于忽略了韩愈体裁的文学而只重视应用散文,其实都不会欣赏,也不去作这种类似韩愈的文学作品了。
韩柳时期开始有了纯文艺的文章,他们都可以文为诗。文章虽随时代而体裁有变,仍有其传统在,如韩文之《原道》《原性》《原毁》及《师说》等等论文,但其精华则不全在此等文章,韩愈亦作“奏议”“序跋”“书说”“赠序”“碑志”“杂记”“辞赋”以及“哀祭”等各类文章,影响后世极宏。与退之同时候写得好文章者厥为柳宗元。
韩柳都是以诗为文,以艺术的日常人生描写出诗的情味,而非宗教式的庄严。退之的《送杨少尹序》,即有诗情画意,为人所爱读。总之,退之之文变化无穷,有各种技巧。
韩愈可以说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至于退之学生,并不出特殊的文才,只有他的姪女婿李翱,其文体似退之,亦作得好。他们这一代过去后,此等新文体的文学已无后继者,要过两百年左右,等宋代的欧阳修出,才有了“文起八代之衰”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