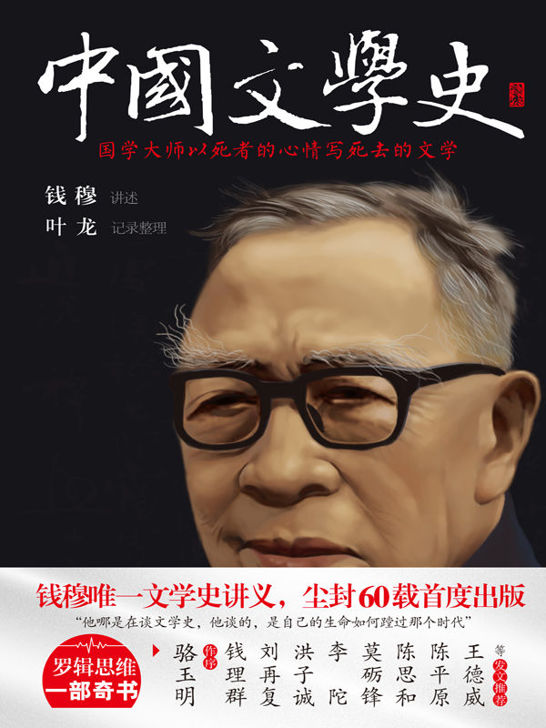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十五篇 宋代古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四十岁被贬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由于永叔四岁时父亡,母便带其三兄妹投奔随州其叔欧阳晔家生活,因家穷,母用荻草在沙堆中教子写字。就在其湖北晔叔家中,得《韩昌黎集》,永叔极喜此书,但并不适用于考秀才进士,待他中科举后,就潜心研习韩文,昌黎文体才借欧阳修得以发扬光大。
某日,欧阳修与二友人出街,见一马踏死一犬。三人相约作一文记之,借此比较孰优孰劣。文成后,三人并不出示各人作品,只问字数多少,以字数最少者为优胜。
由于上述故事,我想起传说中有樵夫改欧阳修文章的趣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常去琅琊山玩,因此与琅琊寺的智仙法师成了好友。智仙为他在游山的路旁盖了一所亭子,落成之日,欧阳修亲自题名为“醉翁亭”,并作《醉翁亭记》一篇。此文原来起首是“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欧阳修原准备刻于亭中石碑,为慎重起见,怕文章有不妥,便抄了五六份遍贴四围城门,征求市民意见,以便修改。即使过路客商、地方官员,亦无不欢迎,但贴了一整天,未见有人提出修改。直到傍晚,有衙役带来一砍柴樵夫欲修改欧文。欧阳修谦虚听命。樵夫认为,该文起首提到东、南、西、北四座山太啰嗦了,于是修欣然遵命改为“环滁皆山也”,一句开首已够,并请苏东坡抄了一份改正后的《醉翁亭记》作为礼物送给樵夫。此故事可能非真,但作文当求简洁、凝练实为写文章的首要。
还有,欧阳修亦不喜作文用冷字僻典太多太杂,令人晦涩难明,但宋祁(注:编者按:宋祁,字子京,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与兄长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因作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世称“红杏尚书”。)撰写《新唐书》时,偏偏用典杂而多。作为主编的欧阳修对此不满,也不好当面批评,于是,稍后当宋祁来欧府赴宴时,永叔在大门上贴了一副怪对联曰:“宵寐非祯,札闼洪庥。”宋祁好奇,看了多遍不得其解,便问永叔门联是何意思。永叔道:因我昨晚得一不祥之梦,所以贴上这副对联以避邪气,意即夜梦不祥,出门大吉。宋祁急问:既然如此,何不直说?要弄得如此费解。永叔道:“我是学你撰《新唐书》的笔法呀!”弄得宋祁哭笑不得。
唐宋八大家中,唐代韩、柳只占两家,其他六家都是宋代人,除欧阳永叔外,尚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轼、辙三父子。除苏洵只小永叔两岁外,其他四位都是永叔后辈,都得过永叔的赞赏和照拂。而且永叔曾说:东坡这位年轻人比我小三十岁,不久将领导文坛(注:编者按:永叔原话曾说,“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永叔亦曾称赞曾巩。苏洵虽只小永叔两岁,亦曾受到永叔与韩琦的称许及举荐,遂名动京师。
欧阳永叔向有推挽后学的好心肠。今再举一例。永叔任滁州太守时,王向在其属下任幹当官(注:编者按:幹当官,本名勾当,避宋高宗赵构讳,改叫幹当。宋代禁军机关之一。北宋皇城司设幹当官七人。)。当地有一位教师因某生拒交学费而告到王向那里,王向批示道:“你应用教鞭惩罚不听教之学生,以树立师道之尊严,何必来向我告状呢?”该教师不服,再上告欧阳修。但欧阳修十分欣赏王向的批示,并夸赞王向之才华且加以提拔,使王向日后出了名。
欧阳修于庆历四年带着满肚怨气来滁州任太守,他本是朝廷的右丞相,因直言敢谏得罪了左丞相夏竦一帮邪党而被贬到滁州。他暇日去逛城外西南的琅琊山,因而结识了一位高僧智仙而成为知己。智仙为他在山腰途中建一亭,让永叔可与民众饮酒同乐,便名此亭为醉翁亭。于是,欧阳修自名醉翁,在此常与智仙及市民醉酒同乐。某日,智仙见亭中喧闹非常,走近一看,原来欧阳修正与几个百姓喝酒猜拳,智仙忙劝他别醉倒了。永叔道:我哪里会醉!民情可使我醉,山水也可使我醉,但酒却不会使我醉。只是如今奸臣当道,借酒消愁,我自装糊涂罢了。于是吟诗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注:编者按:此即《题滁州醉翁亭》。)智仙领悟道:“原来醉翁不醉啊!”同座一位书生模样的中年人起立曰:“太守为官廉正耿直,世人仰慕,公且吟诗一首以贺太守。”诗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泉香鸟语还依旧,太守何人似醉翁?”(注:编者按:此诗相传乃明代苏茂相所作。钱先生所述之故事应为课堂即兴发挥。)众人齐声称好。智仙亦大赞好诗。刻诗于亭碑中,至今仍有。
唐宋古文,韩愈与欧阳修两位均极为重要。欧阳修之文学自韩愈,但两人风格截然不同,韩文有阳刚之美,欧阳修文则是阴柔之美。永叔每成一文,必张贴壁上,一面慢慢朗读,一面慢慢修改,有时甚至将全文改完,一字不留。还有,他的文章读来自然,可脱口而出。如他的《醉翁亭记》,这是一篇杂记。琅琊山在今江苏滁县津浦路附近,永叔在此山筑一亭,前已讲及,不到四十岁,已自称醉翁,作为亭名。其首句“环滁皆山也”,真实情况是由二三百字精改而成,真是神来之笔;也极平易浅近,全文用“也”字。“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一句,即来自此文。总之,永叔作文,精读精改,极为费力也。
作文不能马虎,要学古人榜样,细心改作。像欧阳修的精改细作,确是我们的好榜样。
有人说,欧阳修的学问成就在“三上”,那就是“马上”“厕上”与“枕上”;还有“三余”。傍晚,即黄昏为一日之余;冬天为一年之余;还有“雨天”,也是三余之一。他在这三个余下的时光用功夫、做学问,没有一分钟浪费。
传说,永叔年老时退休还乡,已名满海内外,晚上仍勤读不已。妻子幽默地问道:你还怕老师会骂你吗?(注:编者按:原文为:“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永叔答道:我是怕将来的年轻人要骂我呀!(注:编者按:原文为:“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因此到老仍勤读不倦。
宋人师法韩愈古文最有成就的除了欧阳修,还有王安石。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晚年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也可说是永叔的后辈。永叔曾赞美王安石之文可媲美韩愈古文,但安石则说要学孟子。王安石之文亦具阳刚之美,但与韩文风格不同。
欧阳修有一文《记旧本韩文后》,其中有云:“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之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由此可见永叔之推尊韩文。永叔是两百年后(注:编者按:从韩愈(768-824)至欧阳修(1007-1072)近二百五十年。)真正继承并发扬韩文的大文豪。韩文阳刚而欧文阴柔,这证实了永叔师法韩文是遗其形貌而收其神理气味,王安石赞扬欧阳修,在其《祭欧阳文忠公》中称道曰: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永叔、介甫两人政见容或有异,但论人品之正直同样,又同是宗仰孔孟师道,同是师法韩文公的文章,可谓惺惺相惜,赞美对方绝无丝毫保留,实厚道可风。
就唐宋八大家而言,最重要的当推韩、欧两位。不过我也相当喜欢王安石的文章,因为他熟悉政务,关心政事,所以他的政论文章是我颇感兴趣的。例如,宋神宗登基不久即召见王安石,问宋开国百年来政局粗安情况。安石以《本朝百年无事札》以对,说明政局虽粗致太平,其实乃积弱积贫,亟待改革。安石蒙神宗接待并擢升为参知政事,以实行变法。又如他的《答司马谏议(注:编者按:当时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右谏议大夫。)书》一文,是答复司马光。司马光反对安石的“侵官”“生事”“征利”及“拒谏”四弊政,均为安石驳斥。但此函末尾仍以谦虚及仰慕之心作结。
谈起司马光与王安石,某日开封府尹包拯请他俩同席赴宴,包公屡次劝两人饮,均被拒绝,包公怒极摔杯地上,司马光勉强喝了两口,而安石不饮如故。次日,包公上朝接安石一信,上写一联道:“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包拯遂想起安石之所以拒饮,乃遵照韩愈所言“断送一生唯有酒”及“破除万事无过酒”的警语而行,包公遂恍然大悟,便将对联挂于堂上,以资借鉴。
某次,王安石偕友人游汴京,至管仲鲍叔牙庙时,安石题诗道:“两个伙伴,同眠同起。亲朋聚会,谁见谁喜。”等逛至伯夷叔齐庙,安石又题一诗道:“两个伙伴,为人正直。贪馋一生,利不归己。”当走到哼哈二将庙时,安石再题一诗曰:“两个伙计,终身孤凄。走遍天涯,无有妻室。”同行友人不知三诗有何意义,便问司马光。光答道:这哪里是作诗,这位拗相公只是作灯谜,而谜底却都是筷子。三座庙里不同的神像,却用不同诗句写成同一灯谜,也可见王安石之功力匪浅。
欧阳修的后辈中,还有他当年录取的三个好学生,便是曾巩与苏轼、辙兄弟。
曾巩,字子固,江西抚州人,后居临川,仁宗庆历元年中进士,有《元丰类稿》。欧阳修曾赞道:“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可见他备受欧公重视。
如他的《战国策目录序》,对该书内容抒发个人之意见,为常人所不及。说理清晰,立论精准,为其代表作之一。他的文学见解与文章风格都和永叔相近。朱子曾说:“学文章可从曾巩之文学起。”清代姚鼐也曾说:“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见《复鲁絜非书》。正如林希在曾巩墓志铭中所说:写文章虽然可以开阖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止于仁义(注:编者按:原话为:“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阖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故欧阳修与曾巩之文,正是殊途而同归。
至于欧阳修当年录取的好学生,还有苏轼和辙两兄弟。其中最了不起的是苏轼东坡,他是文学家中的全才,他能作散文、古文、诗、词、书法和画。谈到诗,他是我国四大家之一,即所谓“李白、杜甫、苏轼、黄山谷”。至于苏东坡作文,他自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即是说,东坡作文是无所用心,是出乎自然。故我们又称“韩潮苏海”:所谓韩文似潮是指其刚猛;苏文似海是指其为文平坦无奇,但无所不有。
所谓唐宋八大家,乃是唐代之韩、柳,加上宋代之欧阳、王、曾与苏轼、辙兄弟,再加上苏洵。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可说是一位复古派,但他的文章并不似秦汉格调。韩愈又说“文以传道”,其实,韩的文章并不传道,却是纯文学,也有加入日常生活琐事的。韩愈的复古文风以及文以载道之理想,如没有欧阳修的继起、坚持此种主张,则晚唐五代以来的靡靡之音歪风将无法扭转趋正,所幸永叔所提携的这批后辈,包括王安石在内,还有曾巩,苏轼、辙兄弟在内诸人,均能追随欧公,并力向前,才完成复兴古文的大业。
欧阳修的文章一本正经,以维护孔孟之道为职志,他的词则颇富浪漫情调。有一事可以作证。某年,永叔偶寓汝阳,遇见两位聪明活泼、能歌善舞的歌妓,而且还能背唱欧公作的词,颇得欧公欢心,便约定她们说:我将来一定会来汝阳做太守,可常欣赏你们的美妙歌舞。数年后,欧公果然调来汝阳,却不见两歌女踪迹,欧公不胜惆怅,便作诗道,“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由此可见欧公亦是一位浪漫风流的文人。三十载后,苏东坡亦来此任官,知此轶事后大笑道:这岂非杜牧“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故事重演?
原来晚唐有位大诗人杜牧,某年他去湖州旅游时,遇见一位未成年的美少女,于是凭友人介绍送礼求婚而成功,约定十年后来湖州成亲,接着杜牧奉调回长安任职。转眼已隔十年,他多次要求调职湖州,直至调任湖州太守,此时已距与该少女订婚之日有十四年之久。杜牧到了湖州,才知该少女已于三年前婚嫁他人,并已有三名子女。杜牧恼恨之余,便严词责问该介绍人,对方答以:与君约期已逾三年,当然只好嫁人了。杜牧自知理亏,遂作《叹花》诗道:“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
谈起苏东坡,吾人知道,唐宋八大家中,一家三苏便占去了三位,实在了不起。苏家还有一位苏小妹,文才亦不弱。据说,某日,苏洵与轼父子和小妹三人在月光皎洁之夜限字吟诗。先由苏洵择“冷”“香”两字作为两句之末字各造一句比试。苏洵吟道:“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间过来香。”苏轼则吟出“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两句;苏小妹亦不示弱,吟诗道:“叫月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苏洵苏轼两父子听后,拍手叫好。(注:编者按:钱先生在本篇末讲到,苏东坡轶事甚多。此故事应是钱先生为使课堂生动才讲的轶事。)
其实,我认为每个人的天资是差不多的,一个人要写出好文章,最要紧是要多读书,要能刻苦努力。如苏东坡,他在宋仁宗嘉祐元年西元1056年二十一岁时便考中进士。当年他应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其成绩所以优异,主要是因他博览群籍,广征博引,甚至还自创典故,使作为考试官的永叔大为惊叹,本拟将此文列为第一,由于欧公怀疑此位考生可能是曾巩,为免人说闲话,遂把它压为第二,放榜后才知是苏轼。原来苏轼所作典故,是效仿自《三国志》中的《孔融传》,可见也是从多读书喜读书而得。
苏东坡才华满溢,但喜欢开朋友玩笑。某日与老友刘贡父等小饮,刘贡父晚年患风症,鼻梁几乎塌断,饮酒时各引古人语相戏笑,东坡喜对刘贡父说:“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阖座大笑,贡父怅恨不已,稍后鼻子断烂,忧郁而亡。(注:编者按:此轶事见陈师道《后山丛谈》。)可见开玩笑也得有分寸,不可过分。
东坡此人,不但有才华,还有急智。某年高丽国有使节来访宋朝,上派东坡作陪逛街,谈及作对联,东坡说中国无论男妇老幼,个个都晓。那使者有疑,便顺便将眼前所见路旁宝塔作一上联道,“独塔巍巍,七级四面八方”,命路上老翁作下联。老翁摆手匆匆而去。使节笑道:那老翁不能对,已走远了。东坡道:其实老翁是哑对,他已对出下联,他摆一摆手,意即,“只手摆摆,五指三长两短”,岂非妙对?!高丽使者默然,也足见东坡之有急智。
有关东坡之轶事甚多,就此打住。
苏洵三父子,洵以论辩文最为取胜,其文古雅雄健;苏轼则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诗、词、古文、书、画,样样皆精,为北宋古文运动欧阳修以后的继承者,亦主张“文与道俱”;至于苏辙,其幼年即受父兄熏陶,其文章风格近轼,但成就稍逊,然其文淡泊文静,写景状物,尤为精妙。
有宋一代的古文,当以唐宋八大家中之宋代六人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