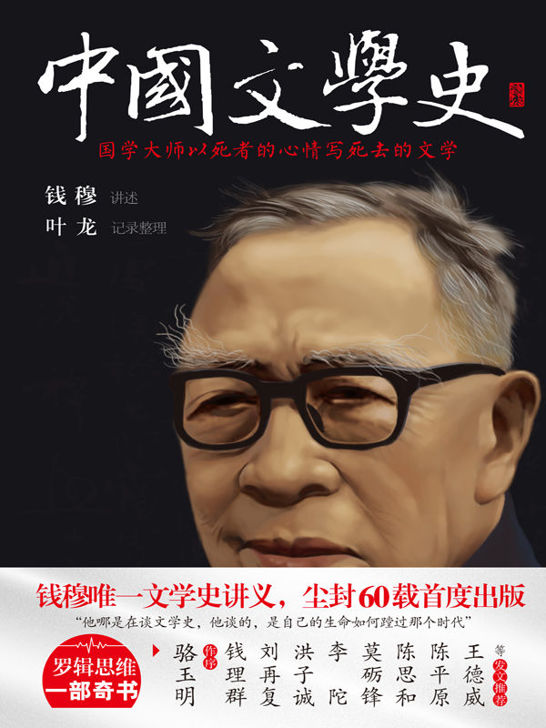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十九篇 明清古文
明代主张复古派的有会所的组织,当时有王世贞明廷大臣等参加。王是主张庙堂派的,文章重雕琢粉饰。
同时期还有归有光昆山人,文章是学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与曾巩,又上学《史记》,特别对《史记》中家常儿女琐事和外戚列传等相当喜好,主张文章出于自然。
后来归有光被认为是文学之正宗。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同时。
学术之伟大在于有自由,且能得到后世的公正评论。谁也不能勉强。
在明代归有光以后,到清代时,古文崇尚唐宋八大家的出了姚鼐,姚的老师刘大櫆,刘的老师方苞,他们三代人都学归有光,均为安徽桐城人。此时考据之学大盛,但桐城派却提倡文学,他们用力最勤的是《史记》,留传有《归方评点史记》(注:编者按:清代广西桐城派古文家王拯编纂了一部《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将归有光、方苞对《史记》的圈点、评论、注疏、考据等有系统地综合在一起,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归有光用红圈,方苞用的蓝圈,两人共圈处则重叠,重要处加圈与三角形,转角的重要处用三角标点;除了点、圈外,还加上注。这是作文章的方法论,师长指示的是一条途径,然后再由自己去跑。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此书是将文体分类,将全国古今文章分为十三类,凡是骈文和骚都归为辞,选入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后,接着选入归有光、方苞和刘大櫆的。但刘文较差,姚鼐将刘大櫆文选入近十篇,人家便说闲话了。人说“归方”“方姚”,而不提及刘,因刘文较差也。
与方苞、姚鼐同时期的是讲汉学的考据学派,他们有门户之见,看不起宋学,但宋代之文学极为有优势。汉学家不喜宋,连文章也不讲宋代人的,他们也不提韩愈,主张恢复学《文选》。
清代出了几位知名学者,他们也学魏晋而不学唐宋。道光年间出了曾国藩,曾氏取进士后到北京,遇见姚鼐的学生梅伯言,后来曾亦学桐城派古文。曾国藩一生在兵营中,仍用功读写文章,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
姚鼐文章学《史记》,曾国藩则学《汉书》,后来称为“湘乡派”,实源自“桐城派”。曾国藩四大弟子中,其中之一为吴挚甫(注:编者按:吴挚甫(1840-1903),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曾长北京大学,严复回国出版著作时必请吴挚甫作序。后来北大国文系内有一派称为桐城派。
另一反对桐城派、讲汉魏的考据派,传至末年,出章太炎,因章师俞樾曲园是汉学家,故章太炎的文章是带有选体(注:编者按:六朝文的代表作品收在《昭明文选》中,所以,又称选体、选派。)味道的。
当时的阳湖派古文家觉得桐城派的文章淡,于是提倡诸子与汉赋。
学《文选》的就穿插了先秦诸子。当时学《文选》和诸子文章的有汪中和龚自珍,章太炎亦然。由于章的弟子在北大教书,故北大也出了选派。北大有选派与桐城派,五四运动出,两派都被打倒了。
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在文学系里听的只是语言、文字与考据而已。三十年来至今,已危险了,致使今日青年已无国文根基。
章太炎年老时在苏州设国学讲习会,这时期他的文章就近似桐城派,别人读来易懂了。他并且教人学文章要自桐城派入,晚年时懊悔自己早不学桐城派。
近代懂得桐城派古文的是梁启超,他认为应学桐城派。但梁启超自己作文不似桐城派,写起来洋洋洒洒,很宽大而散漫,但亦有好文章,例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便是。
我的朋友中,胡适之的文章写来调皮活泼,但用心而不随便写。胡适之的理论我是反对,但他的文章很成功,故至今有影响力。胡的文章仍有点内容,但今人仍不易懂了,因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差了,水准低落了。(叶龙附志一,见篇尾。)
今日青年应能看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如欲在学术界做自由人,一定要花三五年时间读通中英文。如要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必须要读书才是正路。
桐城姚鼐惜抱(注:编者按:姚鼐书斋名惜抱斋。)编纂了《古文辞类纂》,此书主要应先看其序。全书将文章分十三类,如下:
(一)论著;(二)序跋;(三)奏议;(四)书说;(五)传状;(六)碑志;(七)赠序;(八)杂记;(九)哀祭;(十)辞赋;(十一)箴铭;(十二)颂赞;(十三)诏令。
上述十三类中,“论著”“序跋”属于“子”,是关于学术思想之文,序在前,跋在后。例如,杜预注《左传》后,前面写一序。或有在著作完成后请人写序作介绍的,有的则读完该书后写一跋。
接着的“奏议”“书说”“传状”和“碑志”四类,是属于“史”。“奏议”是由下级对上级;“诏令”是上对下;“书说”是游说之文;“传状”是传记,是正式的史;“碑志”则是人死后在坟上立碑,放入坟内的叫墓志,最后几句有押韵的铭,故称墓志铭。此种文体从东汉后而开始盛行至清代。私的史叫碑、状、志,不能正式写传。至于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并不是正经的传。
关于“赠序”和“杂记”,这两类是应酬文。“杂记”是任何东西都可有记,日常家庭小建筑、名胜古迹均可有记。是了不得的应酬,均可有记。如太史公《报任少卿书》是伟大的书信,凭如此一两封信便可留传后世,其后则直到东汉曹操与丕、植三父子才有好的书信。
“哀祭”是属于祭文。“辞赋”“箴铭”“颂赞”三类,则属于应用小品。“辞赋”是有韵之文;“箴铭”是用来鼓励或劝告人的话,均可刻在器物上;“颂赞”则是对画像的颂赞等。
“诏令”类上面已提及,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命令,如君王写给大臣的便属此类。
姚鼐如此分类,是比《昭明文选》进步多了。
但凡一物,有利必有弊,天下事无不如此。中国文风很普及,例如,不可能无数人为一死者作祭文,但每一祭文中必有若干句是精彩的,故后来变成挽联了。
其实对联便是从文章变来的,中国人的对联极有丰富意义与内容。如清代阮元曾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书,又做过云贵总督,滇池有一风景建筑,他作一长数十字的对联(注:编者按:清康熙年间孙髯翁为昆明大观楼作一长联,道光初年阮元改之。),将历史、人物和风景都写了进去。又如,曾国藩与俞樾所作之对联均极佳。因此序跋均可省去,用对联即可取代了。后来,对联太多了,看来就无意义,但大园林名胜仍有极好的对联。例如苏州留园,其中的稻香村有一草亭,上有横匾,刻写了欧阳修的一句话,即是“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此话极恰切,可即景生情。
我国之应酬文后来变成了烂熟,由赠序到杂记,再而变成对联,进而再到打油诗,变俗了。其实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文学要配合人生,古代早已有了,不过只是太烂而已。
徐志摩为欢迎泰戈尔作《泰山日出》(注:编者按: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访华之前,徐志摩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写作《泰山日出》,刊于1923年9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但并不适合东方中国的文学风情。姚鼐的《登泰山记》,无人能出其右,此由于文言辞藻典故多,白话文则及不上。
有一位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曾两次来香港访问我,问及有关泰戈尔的文献中国尚有存否。因泰戈尔曾到过中国,但可惜没有。
今日中国的人生实感枯燥,实足惋惜。
关于传记,西方人十分注重。受西方影响,梁任公写《三十自述》,胡适写《四十自述》。由于中国人经常写作诗文,以后此一生均在此史料中。
清代人写日记是每天记的,伟大的事迹是在日常人生中,均能放入文学中。
桐城派古文的流弊是变成了应酬文,这班古文学家学的是归有光,将此当作文学,但当然亦有好的。(叶龙附志二,见篇尾。)
到曾国藩出,要让文学再回到经、史、子中,他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此书与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不同性格风调。曾国藩有名言曰:“古文无施不可,惟不宜说理耳。”所谓“文以载道”,何以古文不可说理?因唐宋古文家以诗为文,诗是不能说理的,所以曾氏说“古文不宜说理”,原因即在此。
我认为用白话文来抒情是不容易的,由于白话不太能表情之故,所以我说:“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
中国人以诗为戏,散文作得好是可以抒情的,但用白话抒情的则不易见到有好文章。
中国用文言文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
中国的戏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化妆绘画化,集三者于戏剧上。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中国文学史讲到这里,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
唐代的佛经、宋代的语录均有“白话”,但不能肯定此种“白话”是否与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相类似,不过胡适之作《白话文学史》时,都把它划进去了。
如《楚辞》中的“朕皇考曰伯庸”,则绝非白话。
文章有体有用,今日可用白话文描写的文体太少了,只有小说、戏剧、书信、新闻稿及论文等类而已。
中国有两位用白话文骂人的,除鲁迅外,尚有吴稚晖。宁汉分裂(注:编者按:宁指南京,汉指武汉。宁汉分裂指的是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裂。)时,吴稚晖帮蒋介石骂胡汉民而战胜了。鲁迅骂人的文章,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吴稚晖的文章粗俗,鲁迅的则尖酸刻薄而俏皮。平心而论,其《呐喊》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又如他的用古文译的《域外小说集》亦用过功夫,但已较林琴南差了。
共产党的文章长于说理,但文学方面的水准不够,即是说文章没有温情与性情。因文学要靠有温情,热情与冷情均太过了。
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留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
文学在今天已到了非创造不可的时代,全世界都已没落了,英美在今日也已没有大文学家出现。
叶龙附志一:
钱穆老师在本篇中谈到:“今日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差了,水准低落了。”记得一九六○年时,钱师去美耶鲁大学讲学半载,我当时新亚研究所毕业后,在香港一所中学任教文史课程,我有信向钱师问好及报告近况,意外欣喜的是得师逾千字的复函,后辈爱好中国文学的青年朋友,都值得参考,其中有云:
“所谓为人与做学问一以贯之,可即从此体验。最近能精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先从昌黎入门,依次可读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四家,然后再读苏氏父子,读该诸家之诗文时,如能参考读其年谱及后人之评注更佳。在新亚及孟氏图书馆中当可借得。读过姚纂,则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已得其半,即从此两书入门,亦是学问一大道。惟望能持之以恒,不倦不懈,不到一两年即可确立一基础,至盼循此努力为要。《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随笔》《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钞》所选,先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须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惟为学必先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叶龙附志二:
钱穆老师提到的桐城派的古文学家是归有光。另处也提及明代比较好的古文家也只有归有光一人。这是因为桐城派人推尊《左传》《史记》与唐宋八大家古文,而归氏亦相同。如《归方评点史记》即归有光与方苞同有评点《史记》,钱师在篇中已有详细论及。且归氏古文本来就学欧阳修与曾巩。其实方苞评归有光文是好坏参半,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一文中道:
“昔吾友王昆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欤!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欤。此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驳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此处方苞引用两友人对归氏所评,一劣一优,然后方氏本人评归氏亦有优有劣。总的来说,归文在古文义法方法,精于辞章而拙于义理。
至于曾国藩所评,认为归氏之文无法与曾巩、王安石比,亦不能与方苞并举,认为归有光所作赠序、贺序、谢序及寿序等,都是浪费笔墨、无意义之作。但林纾曾替归氏辩护道:“曾文正讥震川无大题目,余读之捧腹。文正官宰相,震川官知县,转太仆寺丞。文正收复金陵,震川老死牖下,责村居之人不审朝臣大政,可乎?……震川文存寿序过多,或其后人爱不忍释,究亦不能病震川也。”(见《畏庐文集·震川集选序》)
桐城派文人中,姚鼐弟子刘开曾谈到作文当循序渐进,谓初学者当先学归、方,然后才进而唐宋八家,再进而至《史记》《汉书》。此番言论是由归、方入门,再进而上溯唐宋八家及《史记》。但归氏之所以能入桐城派文统,主要是归、方同重《史记》,世有《归方评点史记》,且方苞曾称:古文自唐宋八家以后七百年来无人,如无归氏接续,则于桐城派文统有所中断。故刘大櫆、姚鼐对归文加以揄扬,且归文本是师法欧、曾,遂使桐城古文有所承接也。
刘大櫆之喜好归文,曾编《归震川文集》选本,刘氏又曾编选《唐宋八家文钞》,以归文稍得古人行文之意,故将归文附入该书达三十三篇之多。
又,刘氏弟子姚鼐论归文,亦颇多赞赏,其《与陈硕士札》中说:
“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乃华丽非常处。”
此处姚氏说方苞论《史记》不及归氏之深。故归文虽有瑕疵,但亦有其长。姚氏又谓归文风韵疏淡处,深得太史公真髓。因此归文便足以列入桐城文派之列。
另有一问题,钱师于清代桐城派简略提及桐城派方、刘、姚三祖,但所述简略。此处补充若干。笔者1961年时,除在新亚书院担任大一国文讲师外,尚兼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时由钱穆老师指导余研究“桐城派古文”专题,后写成《桐城派文学史》一书,于197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后由钱师推荐敦请港大中文系罗慷烈教授指导余研读硕士,罗师继又敦促余撰写博士论文,并于1998年出版《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一书,港大考试委员饶师宗颐评曰:“论方苞、姚鼐文论要点出于戴名世,具见读戴氏书,用心细而能深入。纠正时贤浅稚之论,尤有于学术界,全文精辟之处在此。”此因时贤论桐城派只及方、刘、姚三祖而未及戴名世南山。此可能由于政治原因,时贤遂不敢道明,然笔者读方、刘、姚三人之古文,均系采集戴氏之意见,予以一一指出,乃前人所未道及,遂受饶师之赞赏。笔者实愧不敢当也。
但在事实上,戴名世在弱冠时,即好交游,与方苞、方舟兄弟极友善;名世亦自言与方苞最亲爱。方苞每成一文,常请名世改定之。凡名世评方文无可取者,方苞则接受意见而毁之。名世自言灵皋(方苞字)尤爱慕余文,时时循环讽诵,想象名世古文中妙远不测之意境,颇有学效并受其影响。
戴名世虽自谦“与灵皋互相师资”,其实是方苞向名世师法,名世长方苞十五年,且名世二十岁前于古文方面已卓然有成,不但于古文写作上,且于古文理论方面,亦多有方苞值得师法之处。
名世既与方苞“往复讨论面相质正者且十年”,方苞于古文方面学自名世者,想不为少。名世作《方灵皋稿序》时为四十七岁,时客金陵。名世三十八岁至四十四岁大部分时间居于金陵,估计两人相与讨论质正十年,当名世三十八岁与四十七岁之间,此时期当为名世文章大成之时,方苞此时取法,得益必大。
名世自言其文章风格曾变化多次。他早期之“放纵奔逸”文风与方苞少时之“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涘”如出一辙;而方苞后期“收敛才气”后之“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鑪锤,穷极幽渺”,则与名世后期之转注于“义理之极微,人情之变态”而“务为发挥旁通之文”亦无以异,此即名世将自己所走创作古文曲折之路之经验授予方苞之明显迹象。则两人所经之途径有如此之雷同实无足怪。两人之见解同,风格同,嗜好古文同,方苞以名世之古文作为范本既达十年之久,其受名世之影响之深且远当可想见。
方苞曾谓:“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可见方氏眼中,唐宋八大家以后,明代无一古文家足以称巨子。方苞之非宗归有光,诚如黎庶昌所言:“望溪为文与归熙甫不类。”然如谓方苞宗法戴名世之文论,则诚离事实不远。且戴、方二人均同宗六经、《论语》《孟子》《史记》及唐宋诸家之文,可谓志同道相合。
至于刘大櫆在古文理论上被认为是创见而最受重视的文论——“神气、音节、字句说”,或称“因声求气说”,其实亦源出戴名世。戴氏所说前人并无特定名称,今姑称之曰“文章魂魄说”。王镇远曾有一文论及,称姚鼐著名的论文八字诀,分明是刘大櫆论文章中“神气”“声音”“文字”的扩充与发展。王镇远并非完全说对。因姚氏所提出为文者八,戴名世大都早已提出过,故姚氏受名世之影响可能更大。其实刘氏的“神气、音节、文学说”并非由刘氏创造,乃源自名世的“文章魂魄说”的启发所得。因名世早在《〈意园制义〉自序》文中说:“每一题入手,静坐屏气,默诵章句者往复十过,用以寻讨其意思神理、脉络之所在。”亦即后来刘氏所提出之由“字句”“音节”而得出“神气”也,其实名世之“文章魂魄说”受方百川之启发所成。但再由方苞稍加发展,即将最精之“魂”——“神气”与最粗之“魄”——“字句”,用稍粗之“音节”贯穿而沟通之,成为更为清晰之文论,而因此再启发姚鼐“为文八诀”之扩展。
换言之,刘、姚之此项文论乃是远绍于名世之“魂魄说”发展而成。
姚鼐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他在《复秦小岘书》中说:“鼐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三者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氏之意是要将义理与考据融化贯通于文章之中,期使文臻乎“道与艺合”及“天与人一”之境界。顾易生谓姚氏此说源自程颐,武卫华则说姚氏此见乃得自刘氏启发,又有近人艾斐谓姚氏此说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创见,其实上述三人说法都值得商榷。因戴名世已早于姚氏提出相同理论,其《己卯科乡试墨卷序》中已说及“君子者,沉潜于义理,反复于训诂”,并且要“言之行世而垂远不可以无文”。这里已提出“义理、训诂、辞章”三者当兼备不可缺一,实已先于姚鼐提出矣!
论者又谓:姚鼐又发明文章“阳刚阴柔说”,其实亦不新,其实此说亦可谓出自名世,因名世有一文《〈野香亭诗集〉序》,其中道:“往余读相国之诗,雄健峭削,如长松千寻,孤峰万仞,而不可攀跻也。今读先生(指相国之子李丹壑)之诗,如清籁在耳,明月入怀,幽微淡远,而难以穷其胜也。”此处便是名世用阳刚阴柔两种境界论同时代友辈之文。前者“雄健峭削,如长松千寻,孤峰万仞”,是明言文章阳刚之美;而后者“清籁在耳,明月入怀,幽微淡远”,则明显是说文章阴柔之美。人又谓姚氏《复鲁絜非书》乃学自严羽之《沧浪诗话》,其实我们如一读名世之《〈意园制义〉自序》一文,便知后者启发姚文更多也。
因此,谈及桐城派如只提方、刘、姚三祖而不提戴名世是不公平的,名世实为桐城派三祖之祖,至少也应该说桐城派有戴、方、刘、姚四祖才对。但为何世人不提名世呢?此乃由于名世因《南山集》遭文字狱之祸而罹难。当时之人莫敢再谈及其文与文论,但今已事过情迁,而饶师宗颐之尊翁饶锷先生慧眼识英雄,在六七十年前对名世之古文特加揄扬,将其古文与欧阳修并称,可谓今之钟子期,名世如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